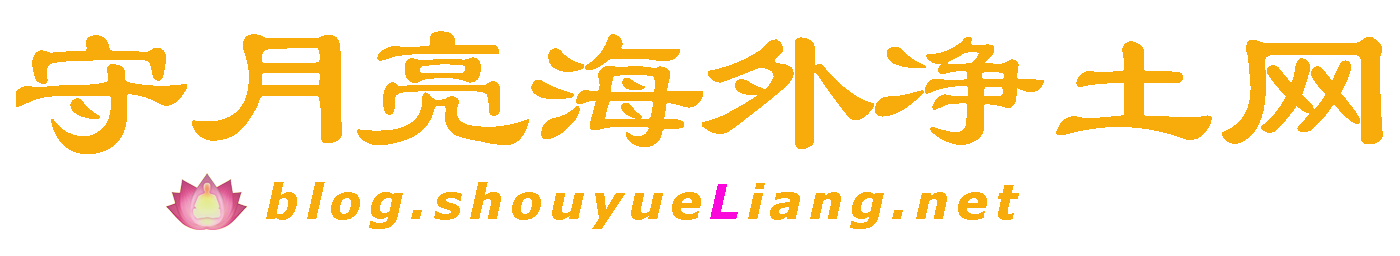称念佛号数次神奇逃过劫难
 已是暮年的我常一边念佛一边在寺院的林间漫步,眼前亦不时呈现着年轻时被佛菩萨放光救助的生动画面,现在把当时的情况写下来,跟大家分享。青年时,我在长沙读书,跟恩师音乐家喻宜萱学唱歌,被《山那边呦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等歌声迷住,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一九四八年,父亲要去台湾,说:“你要想好啊,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出身……”我说:“共产党讲了出身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有这么好的光明大道,我当然要走。爸,最好你也起义投诚!”“孩子,蒋校长待我不薄,再说忠臣不侍二主,我不能不仁不义,背他而去……你既然作了决定,以后若遇艰险时别忘了祖训:念佛能得自在大解脱,做人坚持温良恭俭让……”我跪在地上谢过父母养育之恩,把慈父的话字字刻在心底,洒泪而别。后得知他是白圣长老的弟子。我和同学们在欢喜中迎来了全国大解放,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写墙头标语做宣传,出板报,办扫盲夜校,演《白毛女》《血泪仇》……自编自演活报剧,参加共青团,成了少先队辅导员、团支部书记……一九五七年,为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建设献言献策,我提出了“教材要多加一点孔孟学说”的建议,然由于当时因缘不成熟,一夜之间,我被打成“右派”。当时,佛教在大陆还没恢复,我一边在心底默念佛号,一边反思自己没好好听父亲的话,让工作上的小顺利冲昏了头脑,这对贡高我慢的我来说是一次最深刻的教训。因我检查反省深刻表现好,很快重新恢复了工作。一九六五年,由于我业余时间为孩子们写过一些小文章,受邀到庐山参加了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一九六六年,因父辈亲人均在海外,我受运动波及,多次受审揪斗。有几次被批斗得太厉害了,我内心在绝望中大声呼叫:“阿弥陀佛!”只见光圈罩下来,他们看不见我了,撒手而去,逃过一劫。有一次,深夜在野外武斗,我被斗得实在受不住了,大呼:“阿弥陀佛!”一道光圈射下来,突然不知什么力,把他们推到荷塘中央。从此,他们不敢再武力批斗我了,但加强了对我的劳动改造,把我放到七山林场挑煤、打柴、开荒、植树、种地、养猪……限时挑煤一担一百斤,没完成任务则挨打,少一斤便抽一皮鞭,晚回一分钟也一皮鞭,有几次我在半路实在挑不动了,大哭大喊“阿弥陀佛”,突然,我的学生和家长从光圈中走出来,悄悄地接过担子,帮我按时按量地完成任务,其他的劳动任务也都如此顺利完成。后来把我的劳动任务分给三个人做才能完成。打也打不垮,劳动也累不垮,把我密关小屋内饿几天几夜……开头一两天,我勉强经受住了,到第三天我实在饿得不行了便大哭大喊:“阿弥陀佛,我是郭子仪后人,世代军旅,杀业太重,我罪有应得,挨打挨饿,我自作自受——若我寿命尽了,请阿弥陀佛接我往生,如寿命未尽,请阿弥陀佛帮我度此饿关!”一道亮光照射来,只见关我的小木屋中一个大土砖被掀开了,饭菜从闪光的洞口送了进来,听到有人道:“老师,听你哭喊我们才知道你关在这里挨饿,饭食不好,您将就着吃吧。”康海兰同学和她的家长在我生死攸关时巧妙地送来了救命饭。我和着泪狼吞虎咽地吞下饭后,又把土砖轻悄悄地塞好。因此,这些人觉得奇怪,一打不死,二累不死,三饿不死……难友们见我秘密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有这么多神奇妙用,也都悄悄地跟我学佛念佛。从此,我们难友中再也没有自暴自弃寻短见的人了。平反昭雪后,我们成了念佛修行的知音。离休后,我们投入修建寺院的活动,我们又用在劳动改造中学来的技能栽花种果,其乐融融。真得感恩在危难时所历经的锻炼,有很多事只有透过实证才知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人生能有此锻炼方能得真智慧真性情!如今,莲友们日渐衰老,在东林寺大安法师的教导下,我们从不怨天尤人,天天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我们相约临终前加紧持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心被时时朝着西方的信念盈漾,我们深信:在莲台清香摇曳中,阿弥陀佛的金色手臂时时伸向我们每一个人,让每一个实愿实信的人都能在幸福愉快中安详地走进阿弥陀佛慈父的光圈中,降落在阿弥陀佛慈父的手心里,接引到西方莲台上……声明:本文摘自《净土》杂志2017年第4期,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删除。
已是暮年的我常一边念佛一边在寺院的林间漫步,眼前亦不时呈现着年轻时被佛菩萨放光救助的生动画面,现在把当时的情况写下来,跟大家分享。青年时,我在长沙读书,跟恩师音乐家喻宜萱学唱歌,被《山那边呦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等歌声迷住,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一九四八年,父亲要去台湾,说:“你要想好啊,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出身……”我说:“共产党讲了出身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有这么好的光明大道,我当然要走。爸,最好你也起义投诚!”“孩子,蒋校长待我不薄,再说忠臣不侍二主,我不能不仁不义,背他而去……你既然作了决定,以后若遇艰险时别忘了祖训:念佛能得自在大解脱,做人坚持温良恭俭让……”我跪在地上谢过父母养育之恩,把慈父的话字字刻在心底,洒泪而别。后得知他是白圣长老的弟子。我和同学们在欢喜中迎来了全国大解放,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写墙头标语做宣传,出板报,办扫盲夜校,演《白毛女》《血泪仇》……自编自演活报剧,参加共青团,成了少先队辅导员、团支部书记……一九五七年,为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建设献言献策,我提出了“教材要多加一点孔孟学说”的建议,然由于当时因缘不成熟,一夜之间,我被打成“右派”。当时,佛教在大陆还没恢复,我一边在心底默念佛号,一边反思自己没好好听父亲的话,让工作上的小顺利冲昏了头脑,这对贡高我慢的我来说是一次最深刻的教训。因我检查反省深刻表现好,很快重新恢复了工作。一九六五年,由于我业余时间为孩子们写过一些小文章,受邀到庐山参加了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一九六六年,因父辈亲人均在海外,我受运动波及,多次受审揪斗。有几次被批斗得太厉害了,我内心在绝望中大声呼叫:“阿弥陀佛!”只见光圈罩下来,他们看不见我了,撒手而去,逃过一劫。有一次,深夜在野外武斗,我被斗得实在受不住了,大呼:“阿弥陀佛!”一道光圈射下来,突然不知什么力,把他们推到荷塘中央。从此,他们不敢再武力批斗我了,但加强了对我的劳动改造,把我放到七山林场挑煤、打柴、开荒、植树、种地、养猪……限时挑煤一担一百斤,没完成任务则挨打,少一斤便抽一皮鞭,晚回一分钟也一皮鞭,有几次我在半路实在挑不动了,大哭大喊“阿弥陀佛”,突然,我的学生和家长从光圈中走出来,悄悄地接过担子,帮我按时按量地完成任务,其他的劳动任务也都如此顺利完成。后来把我的劳动任务分给三个人做才能完成。打也打不垮,劳动也累不垮,把我密关小屋内饿几天几夜……开头一两天,我勉强经受住了,到第三天我实在饿得不行了便大哭大喊:“阿弥陀佛,我是郭子仪后人,世代军旅,杀业太重,我罪有应得,挨打挨饿,我自作自受——若我寿命尽了,请阿弥陀佛接我往生,如寿命未尽,请阿弥陀佛帮我度此饿关!”一道亮光照射来,只见关我的小木屋中一个大土砖被掀开了,饭菜从闪光的洞口送了进来,听到有人道:“老师,听你哭喊我们才知道你关在这里挨饿,饭食不好,您将就着吃吧。”康海兰同学和她的家长在我生死攸关时巧妙地送来了救命饭。我和着泪狼吞虎咽地吞下饭后,又把土砖轻悄悄地塞好。因此,这些人觉得奇怪,一打不死,二累不死,三饿不死……难友们见我秘密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有这么多神奇妙用,也都悄悄地跟我学佛念佛。从此,我们难友中再也没有自暴自弃寻短见的人了。平反昭雪后,我们成了念佛修行的知音。离休后,我们投入修建寺院的活动,我们又用在劳动改造中学来的技能栽花种果,其乐融融。真得感恩在危难时所历经的锻炼,有很多事只有透过实证才知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人生能有此锻炼方能得真智慧真性情!如今,莲友们日渐衰老,在东林寺大安法师的教导下,我们从不怨天尤人,天天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我们相约临终前加紧持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心被时时朝着西方的信念盈漾,我们深信:在莲台清香摇曳中,阿弥陀佛的金色手臂时时伸向我们每一个人,让每一个实愿实信的人都能在幸福愉快中安详地走进阿弥陀佛慈父的光圈中,降落在阿弥陀佛慈父的手心里,接引到西方莲台上……声明:本文摘自《净土》杂志2017年第4期,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删除。